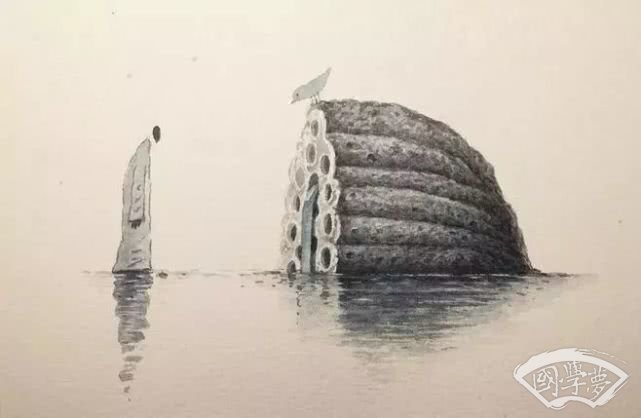
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功夫,乃有益。若只好靜,遇事便亂,終無(wú)長(zhǎng)進(jìn)。
——《傳習(xí)錄》
“閉門即是深山,讀書(shū)隨處凈土。”
相信很多人都十分喜愛(ài)明代文學(xué)家陳繼儒的這句話。
含蓄內(nèi)斂的中國(guó)文人生性多好靜,總是渴望關(guān)起門來(lái),靜棲一處,將塵囂隔離在外,留一方風(fēng)清月朗的小天地,一卷書(shū)也好、一盞茶也罷,便足以對(duì)抗人世間萬(wàn)般無(wú)趣。
然而好靜到極致,難免不接地氣、落落難合。王陽(yáng)明因此常告誡我們,要警惕“靜”的陷阱。
他說(shuō):“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工夫,乃有益。若只好靜,遇事便亂,終無(wú)長(zhǎng)進(jìn)。”
一個(gè)人須常在事上磨練做工夫,如此才會(huì)真正成長(zhǎng);如果只是一味追求清凈,遇事難免自亂陣腳,終究不能有所進(jìn)益。
有位名叫劉君亮的門人曾想要去山中靜坐。
王陽(yáng)明勸他:“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,是反養(yǎng)成一個(gè)驕惰之氣了;汝若不厭外物,復(fù)于靜處涵養(yǎng),卻好。”
在陽(yáng)明先生看來(lái),一個(gè)人若抱著厭離的心態(tài),刻意離塵絕俗、尋求清靜,反而容易長(zhǎng)養(yǎng)驕慢懶惰的習(xí)氣,看似潔身自好,其實(shí)是自許清高、消極逃避。
生活中常見(jiàn)這樣的人,受不得柴米油鹽的辛苦,見(jiàn)不得人情世故的瑣屑,不甘心腳踏實(shí)地做尋常事,更不屑于真心誠(chéng)意地與人相交。
抱著厭離之心一味追求清靜解脫,往往容易落得乖張偏執(zhí),不僅難以抵達(dá)虛設(shè)的詩(shī)與遠(yuǎn)方,反而容易將當(dāng)下的人生過(guò)成一地雞毛。
還有位門人曾請(qǐng)教王陽(yáng)明:“靜時(shí)亦覺(jué)意思好,才遇事便不同,如何?”
平靜無(wú)事時(shí),覺(jué)得自己修養(yǎng)甚好,凡事看得通透明白,可是一遇到不合意處,就瞬間打回原型,涵養(yǎng)盡失,該如何是好?
王陽(yáng)明回答:“是徒知靜養(yǎng),而不用克己工夫也。如此,臨事便要傾倒。”
在陽(yáng)明先生看來(lái),一個(gè)人若只在無(wú)事時(shí)養(yǎng)靜,缺少具體事上切切實(shí)實(shí)的磨練,就很難真正做好克己工夫,這樣的境界就像空中樓閣,經(jīng)不住現(xiàn)實(shí)境遇的考驗(yàn)。
身為凡夫,很容易復(fù)制這樣的情形,就連蘇東坡的修行也未能免俗。
東坡曾寫信給佛印和尚,說(shuō)自己最近修煉到“八風(fēng)吹不動(dòng),端坐紫金蓮”,也不貪婪了,也不嫉妒了,也不生氣了,任爾東西、如如不動(dòng)。
誰(shuí)知佛印和尚大筆一揮,在信上批了“放屁”二字退回,把東坡氣得半死,馬上跑到金山寺大罵佛印。
佛印見(jiàn)東坡氣急敗壞的樣子,哈哈大笑地調(diào)侃他:“八風(fēng)吹不動(dòng),一屁打過(guò)江。”
東坡一聽(tīng),恍然大悟,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(lái),后來(lái)還把玉帶贈(zèng)給金山寺作為鎮(zhèn)寺之寶。
所謂“歲月靜好”往往會(huì)帶來(lái)一種錯(cuò)覺(jué),我們自以為已經(jīng)修煉到“八風(fēng)吹不動(dòng)”,卻依然會(huì)為一句“一屁打過(guò)江”而暴跳如雷。
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認(rèn)身而為人的局限,實(shí)實(shí)在在、認(rèn)認(rèn)真真地活一次,這或許是更好的修行。
“吾生好清凈,蔬食去情塵”、“晚年唯好靜,萬(wàn)事不關(guān)心”,這樣的境界美則美矣,卻未必適合任何人的任何生命階段。
動(dòng)靜如一,如果你追求的靜,只是出于對(duì)靜的沉湎,那么不過(guò)是在順從自己求靜的欲望,心中并無(wú)清靜可言。
關(guān)鍵詞:王陽(yáng)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