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詩經(jīng)》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集,所民歌詩詞眾多,主要是當(dāng)時(shí)人們生活的反映。既有愛情婚姻,如“關(guān)關(guān)雎鳩,在河之洲”,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華”,還有勞動人民的日常,如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戶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,相信看過詩詞大會的朋友都很熟悉。戰(zhàn)爭這一主題,自古都是詩詞的重要議題,在詩經(jīng)中多有體現(xiàn)。盡管在很多時(shí)候戰(zhàn)爭只是為了實(shí)現(xiàn)目的不可避免的一種手段,但簡單的得失背后到底有多少出征將士的血淚?“興亡”二字又道盡了多少無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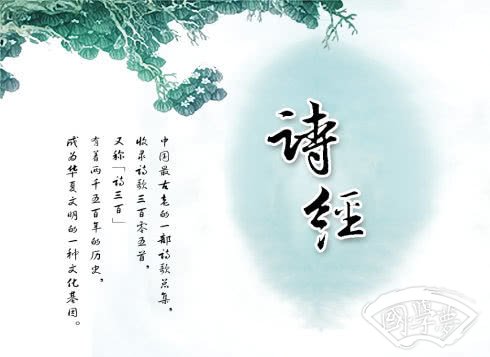
詩經(jīng)當(dāng)中有一首名篇真實(shí)寫出了普通士兵在面臨戰(zhàn)場大局時(shí)內(nèi)心的掙扎和悲哀,讀完之后,感到心酸之余又不免有些慶幸。慶幸戰(zhàn)爭的陰云遠(yuǎn)離了現(xiàn)在的我們,卻又不由得為當(dāng)時(shí)人們因戰(zhàn)爭流離失所的命運(yùn)感到哀嘆。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《擊鼓》。
這首詩共有五章,其中的第四章經(jīng)常被后人用來指代夫妻之間真摯又不可割舍的感情。然而在最初,這句詩只不過是用來表達(dá)出征的將士與其生死與共的戰(zhàn)友之間的兄弟情誼。下面我們就來進(jìn)入詩中描繪的世界。
擊鼓其鏜,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,我獨(dú)南行。
從孫子仲,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,憂心有忡。
爰居爰處?爰喪其馬?于以求之?于林之下。
死生契闊,與子成說。執(zhí)子之手,與子偕老。
于嗟闊兮,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,不我信兮。

邊疆的戰(zhàn)鼓聲聲作響,如我一樣的普通士兵都在將軍的指揮下進(jìn)行日常操練。可是為什么偏偏是我跟著軍隊(duì)來到了這里?然而家鄉(xiāng)有很多人卻與我不同,即便是每日在城墻下服役也好,總能夠避免離鄉(xiāng)之苦。我們聽從軍中統(tǒng)帥的安排,遠(yuǎn)離故土幫助盟國陳國。可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,我的心中怎么能安寧?
究竟有哪里可以讓飄零在外的我暫時(shí)停歇?一直陪伴我的馬兒丟失了,我又要往何處去尋找?我追尋著馬兒的痕跡,卻發(fā)現(xiàn)它已經(jīng)自由的生活在山林中。我和戰(zhàn)友早就發(fā)誓要生死與共,那么在上戰(zhàn)場的時(shí)候也攜手一起度過吧!可我還是擔(dān)心我們兩個(gè)會因戰(zhàn)爭生死相隔,沒有機(jī)會守住最初的誓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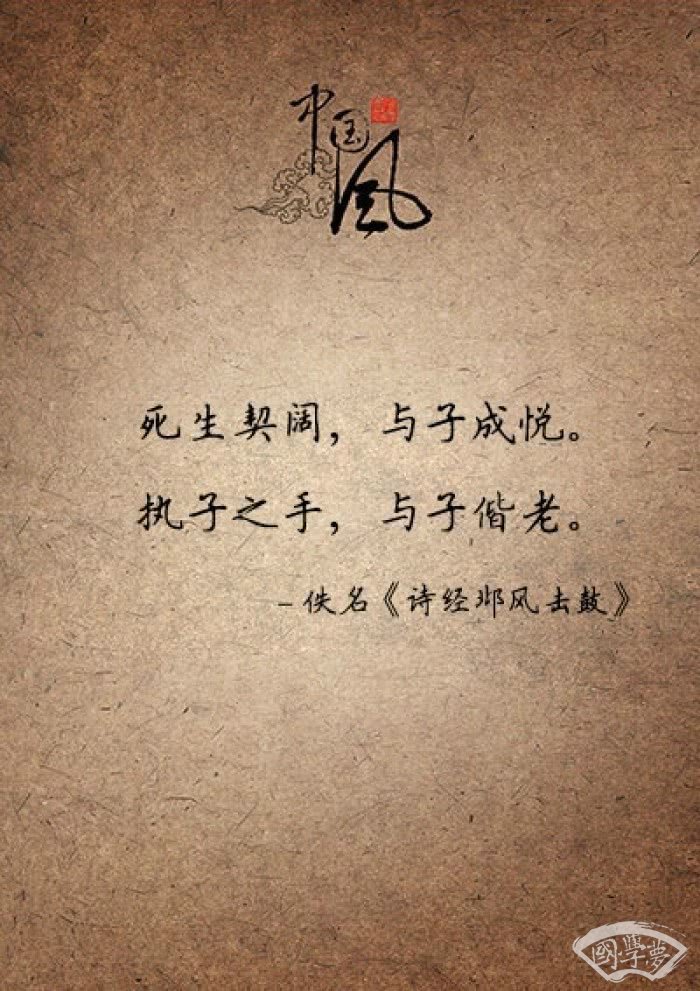
這首詩最妙的地方在于由小及大,從戰(zhàn)場上一個(gè)普通士兵的角度道盡戰(zhàn)爭的殘忍和泯滅人性。詩的開頭簡單幾筆就刻畫出了軍營中備戰(zhàn)的情景,而后卻直接由士兵說出他對離鄉(xiāng)遠(yuǎn)征的不愿。隨后又指明了這場戰(zhàn)爭主要是為了幫助盟國這一意圖。可就是因?yàn)榫踔g的野心,便要無數(shù)個(gè)“我”背井離鄉(xiāng),冒著生命危險(xiǎn)征戰(zhàn)。
借由戰(zhàn)馬脫逃只為追逐自由這件事,說明遠(yuǎn)離戰(zhàn)爭去追求平靜幸福的生活本來就是人的天性。不過即便是在充滿殺戮的戰(zhàn)場,其中也是有人性的閃光點(diǎn)的。比如說“我”和戰(zhàn)友之間的可貴情誼。然而就連這一點(diǎn)都要被戰(zhàn)爭無情的奪去,二人就連同生共死都很難做到。

以“我”的角度出發(fā),待到讀者完全代入到“我”這個(gè)角色之后更能發(fā)人深省。“我”的不愿,渴望,擔(dān)憂,再到最后就連“我”想要擁有的一切都成了奢望。同以往很多借助古跡或者史實(shí)描寫戰(zhàn)爭的詩作不同,詩經(jīng)里的這首詩并沒有過多的修飾,完全只是以情動人。然而就是這種最質(zhì)樸的角度,才會更讓人對戰(zhàn)爭的殘酷有切身的體會。這也是它能夠在千年后的今天還為人稱頌的原因。讀者朋友們,你們喜歡這首詩嗎?歡迎留言與我一起探討哦。
關(guān)鍵詞:詩經(jīng)